《"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假如在这时候还来谈“无政府主义”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虽然“无政府”被标签成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的同义词,确实是有点冤枉的。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主动的,不像今天一般的老百姓那样,顶多只是消极且被动地在咖啡店骂政府的娘,骂生活的娘,骂老板的娘。
我觉得,在报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就很具有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精神。当然,敲敲键盘或摇摇笔杆就能换取一定的稿费、名声,以及达到消磨时间的目的,或许也能算是写作额外的附加价值。
对大多数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来说,投稿的最主要推动力,恐怕不是来自于稿费、名誉,或消磨时间。按照几位同样有投稿经验的朋友的说法,以及个人的推敲所得,我猜想,为了满足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今天社会上的冷漠,除了表现在远亲、近邻同样不值得期待,在报章言论版面上讨论的稀少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往往让写作人不自禁地感觉纳闷,怎么自己费了老大的劲儿写出的成果,居然就像是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呢?
传达意见只是表象,交流意见才是核心。达不到交流目的的写作,终归满足不了一般写作人“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狗吠火车其实盼的也是火车偶尔会传来“嘟”的一声“回响”,何况是人?
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写作人,不时主动地以敏感的课题,或挑衅的语句,企图刺激读者的神经线。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希望能够唤起共鸣,即使没有共鸣也希望有人会忍不住拍马而上,交流一下意见。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对牛弹琴般的毫无反应,偶尔有反应了,却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逻辑与立场,一心只是想到要“赢”,完全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数年前曾经因为文章中一句尼采的话引来回应,可惜对方摆出的姿态就是“我对你错”,“我赢你输”;我这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胜负心,既然无意交流,那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要赢就让你赢吧。那篇文章“让你赢”的意见被编辑删改得烟消云灭、不露痕迹,恐怕最后大家都不知所云,什么目的也没达到。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十分遗憾。
不久前,一位在电子报上写文章的朋友,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华人的问题》(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585.html)的文章,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总得被乱箭射成刺猬了吧?不料却连一则回应都没有。朋友十分泄气,问我现今的读者到底是冷漠?还是麻木?是否该写篇《马华,我爱你!》才会有反应?对于他的疑问,坦白说,我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可以提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假如这家伙果真写了这么恶心的文章,我第一个就绝对不回应他!
27/03/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真是凑巧,《华人的问题》有人回应了,可惜又是个条件反射式的回应。本想去插几句话,但《独立在线》规定得先注册才允许留言,还是算了吧。
Saturday, March 27, 2010
Sunday, March 07, 2010
《人生如戏》>>26/02/2010《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沈观仰老师
《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今日的专业人士无法代替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再是以“人”作为中心的世界,而更倾向于一种自我中心的、或非人的世界。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启蒙时代以来,这种独尊科学的风气,导致诸神的隐退,而科学以外的真理,不论是以诗歌、神话或宗教做出的诠释,一概被消音。这种单元的局面并不利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邱家金教授主张的单元文化爱国论,与此种风气有其异曲同工之“不妙”;不知学历史出身的邱教授在学界饱受科学教条的边缘化之后,何以还对单元文化的霸道表现得如此麻木不仁?
假如今天知识分子还没有绝种,现代社会似乎至少也已成功地将知识分子推向绝种的边缘,以致有类似雅各比(Russell Jacoby)发出的“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呼声。传统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彼岸世界,成了现代性无法即时消费的奢侈品,而凡是不能马上消费或消化的不论具体还是抽象的物品、概念、文化,在今天都注定难以引起广泛的兴趣。在教育普及后,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也不再足以建立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先知、伟大导师、甚至救世主般的威望;而且,就有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常强调的,科学知识是具有“可错性”的,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不也是如此吗?知识确实不是真理,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理,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受缚于自身的狭隘与无知。
今天我们比过去更明白知识分子不是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而且我们也不再要求有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的打救或承诺。但是,假如我们对世界仍有一些追求与盼望,那还有谁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除了传统知识分子,还有谁是既有知识,又有德性,对世界抱有价值信念、终极关怀等普世精神的,加上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能力的呢?现代社会造成的精神危机让传统知识分子退出舞台中心,但偶尔听见一些微弱但铿锵有力的呼声,虽然不造成太大的影响,至少证明了人的良知不死。知识分子的少见或许只属于暂时性的现象,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知识分子并没有绝种;就像曾于1898年被认为已经绝种,却在1948年又被重新发现的纽西兰泰卡鸡(Takahe)一样,我们期待着知识分子的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总是一个值得期待兑现的承诺。柏拉图洞穴中的黑影也不全然就是幻像而已;再说,有影子表示光明就在不远处,未来还是乐观的。吾师徐岱教授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良好的知识,2.对“善”的真诚关注,3. 持久的毅力。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愿意,很多人都有这个潜能。
依愚见,邱家金教授爱说什么都应该有他的自由,任何人的发言权我们都理应给予尊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为一些不中听的话太生气,尤其不必因为这些不中听的话是由一位教授说出来就生气。不就是教授而已嘛,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仙,似乎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我国的华文教育仍有改善的空间是个事实,有意见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论,但华文教育岂会因为某个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崩溃了吗?当然不会的,我国华文教育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脆弱了呢?同样道理,当伟大人物赞扬华文教育的成就,那也不值得我们洋洋得意、信以为真。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在于言论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发言人的立场,更无关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具备这样的态度才算得上实事求是,讨论方不至于动不动就陷入互丢泥巴的苦战之中。
姑且不论沈观仰先生对我个人这一句“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评语到底有几分道理,但是坦白说,自己对知识分子确实还是有所期待的。你们又怎么看呢?
26/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5/02/2010《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3、24/02/2010《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22/02/2010《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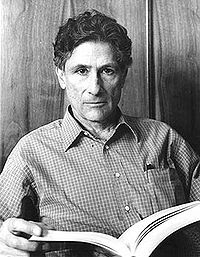
萨义德
缘起:不久前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的一些言论,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据个人浅见,这主要关系到大家对邱教授社会定位的认知与期盼出现落差之故。在此无意对邱教授言论再加以置喙,只是希望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进行一个探讨。在厘清学者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后,相信许多人就会对邱教授的言论顿感心平气和。“知识分子”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什么是知识分子呢?这里将以四篇短文表述我个人的看法。
《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从古至今,由西到中,不论是文人、爱智者、智者、学者、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将这些称谓串连起来的核心就是“知识”。孔子强调“智、仁、勇”,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也有“智慧是一种德性”(1105)的说法,智慧是知识的升华,由此亦可见“知识”向来就是被高度重视的一个元素。但是,上述各种同样都是具有知识的人,给予我们的印象却大不相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人投以怀疑的眼神已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似乎也唯有“知识分子”过去高大形象的消退,最让人耿耿于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知识以外,还拥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素质,譬如德性。再说,专业人士的出现,无疑也模糊了知识分子的面容。
所谓“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而是安置在他人身上的一种标签。鲍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一书中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鲍曼在此处划定的“全体国民”显然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知识分子说话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圈子,他需要具备的是更普世性的关怀。已故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更应该“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同时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就班达(Lewis Benda)的标准而言,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价值,“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
诚然,任何给予知识分子的定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绝对的定义,否则即犯上了怀海特(Alfred N. Whitehead)所说的“完美字典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perfect dictionary)。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正如我国民间学者沈观仰先生于2000年8月27日借《南洋商报》所提出的:在今天知识分子真的没落了吗?假如没落了,我们是否应该接着问:那么,知识分子还值得我们期待吗?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似乎都被市场经济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语道破,专业人士关心的是“技术作用而非批判作用,统治而非激进变革,组织效率而非意识形态的功能性,适应而非对立。”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人,专业人士则提供工具性知识;传统知识分子关心“应该是什么?”(ought)的伦理问题,专业人士则关心“是什么?”(is)的知识问题;传统知识分子重视事物的终极价值,专业人士重视的是事物的工具价值,或者可提供交易的价格。
自斯多葛派之后,二千年来知识分子都在贬斥现实主义激情、倡导超越性,然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并不具备经济价值,因而在现代社会似乎已失去了应有的空间。可是,萨义德直言:“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人文关怀与经济价值原就不应该相提并论。当然,他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之间完全不存在交集的极端情况,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却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常让人弄不清楚孰是珍珠孰是鱼目。大学教授可算是专业人士吗?怎么样的教授才攀得上知识分子的殿堂?这对我们的眼界的确是一种考验。在此不妨根据吾师徐岱教授在课上提出的建议,且把知识分子分成书斋型和社会型两大类来考虑。我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尝试个别做思考。
延伸阅读:[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题为《知识分子还值得期待吗?》,文章一分为四,《南洋商报》连续五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19/02/2010《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Subscribe to:
Posts (Atom)